文 | 硅谷 101
8 月 6 日,#台积电 2nm 工艺突然泄密的话题冲上热搜第一,大家再次把视野聚焦到了芯片制造行业。而这个行业中绝对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光刻机,以及制造它的王者阿斯麦(ASML)。
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疑问,芯片制造触碰到了物理极限了吗?为什么技术进步如此缓慢?而人类会被锁死在 1nm 吗?

这期视频,我们将从技术角度,详细聊聊光刻机的现状与未来。
作为世界上最赚钱的机器,它的核心部件,全球仅有两人能手工维护;更离奇的是,只需几个“屁”,就能让这台价值数亿美元的机器,减产几小时。
ASML 新一代 High-NA EUV 光刻机造价飙升,英特尔抢先入手,台积电又为何却犹豫不决?早就拿到了 High-NA EUV 的英特尔,为何依然没有量产 2nm 以下的芯片?
而不怎么知名的日本厂商 Rapidus 又为何开始了 2nm 的试产?光刻机又将如何突破物理与成本的“双重围剿”?
AI 如何成为它进化的“新燃料”?而善于制造精密机器的 ASML,又为何多次因“低级疏忽”导致股价大跌呢?
01 拆解光刻技术:锁死芯片命门的物理咒语
拆开一台 DUV 光刻机,就会发现其实光刻的原理非常简单。

首先是光源(Source)模组,负责发射波长很短的光,穿过印有芯片电路图的掩膜版(Mask)、光瞳(Pupil)以及一组硕大的透镜组,将掩膜版上的图像,等比缩小打到涂有光刻胶的晶圆(Wafer)上,这就完成了一次光刻。
这个过程就像我们小时候的一种玩具,在激光笔前面加一个刻有图像的透镜,就能打出成倍放大的相同图像。在光刻机中光路则是反过来、成倍缩小的。
当然芯片制造的流程远不止光刻这一步,光刻胶被照射后会硬化,后续还要经过显影、刻蚀、光刻胶去除、离子注入、薄膜沉积等步骤才能成为芯片。

芯片是由晶体管构成,同样面积下晶体管越多,芯片性能也就越强。而光刻机的分辨率越高,就能打印出更小的电路图。
在 ASML 各地办公室的墙上,你都可以看到这样一条公式:CD 等于 K1 乘以λ除以 NA,这就是瑞利判据(Rayleigh Criterion),决定了光刻机的分辨率上限,也意味着要缩小芯片制程,要么降低 K1 和λ、要么提高 NA。

02 光的波长λ
大家经常听到的“EUV”、“DUV”光刻机,是按照使用光源的波长来分类的。上一代光刻机采用深紫外光(DUV),如今最尖端的使用了极紫外光(EUV)。

接下来我们看看 EUV 是如何产生的。
Chapter 2.1 LPP 技术:每秒十万次轰击
注意看,这条细细的线,其实并不是一根线,而是以每秒 5 万颗速度喷出的锡滴,每颗锡滴大小为 30 微米,只有头发丝的一半。

喷出这些锡滴的喷嘴经常会被堵塞,而要更换喷嘴,需要将两根几乎看不见的线,精细地缠绕在喷嘴处,这个过程无法使用任何机器,全球只有两个人可以手工完成,其中一人名为 Joann。所以有这么一句话,“与 Joann 握手时,请务必小心!”。
这个喷出锡滴的装置,就是 ASML EUV 光刻机的光源模块。光源模块可以说是光刻机中最核心的部件,如何“稳定”且“高功率”获得波长更短的光,就是光刻机进步的挑战之一。我们先来看看 ASML 是如何产生极紫外光的。
他们首先将高纯度的液态锡,利用惰性气体施压,喷出成锡滴,也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细线”,然后先用能量较低的激光轰击,将锡滴打成饼状,再用高能量的激光轰击锡饼,形成等离子体,此时就会辐射极紫外光,再通过收集镜捕获,传递到掩膜版和镜片组。

但每次操作只能产生零点零几秒的光,所以才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每秒需要喷出 5 万颗锡滴,同时激光要完成 10 万次打靶,才能产生稳定的 EUV 光源。这被称为激光等离子体光源,简称 LPP(Laser-Produced Plasma)。
虽然 EUV 光刻机 2019 年才正式投入商业量产,但 ASML 第一代 EUV 光刻机早在 2010 年就生产出来了,而当时无法投入量产的原因就在于,光源部分的功率不足,只有不到 10W,这就会导致每颗芯片需要曝光的时间更长,最终每小时只能生产 5 到 10 颗芯片。

直到 2017 年 7 月,EUV 光源功率达到了 250W,才得以推动 EUV 光刻机的商业化,到 2023 年时,ASML 的光源功率提升到了 600W,如今正在攻克 1000W 的目标。
这也意味着目前的 EUV 光源还会使用很多年,短期内要降低芯片的制程,不会从光源入手。

Leo Pang(庞琳勇) 斯坦福博士、SPIE Fellow 美国 RevoLinx 公司总裁: 大家一般是不喜欢变光源的波长,因为光源的波长不只是跟光刻机有关。曝光了之后,相当于要去做显影,然后才能把图案做出来,针对不同光的波长的(Photo)Resist(光刻胶),其实它是完全不一样,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换下一个光源。但是一个光源,一个波长的话会持续很多代,(EUV 光源)至少会(用)到 2035 年到 2040 年。
Chapter 2.2 DPP、LDP、SRS、FEL 等其他技术
除了 ASML,市场中的其它玩家也在想办法攻克极紫外光的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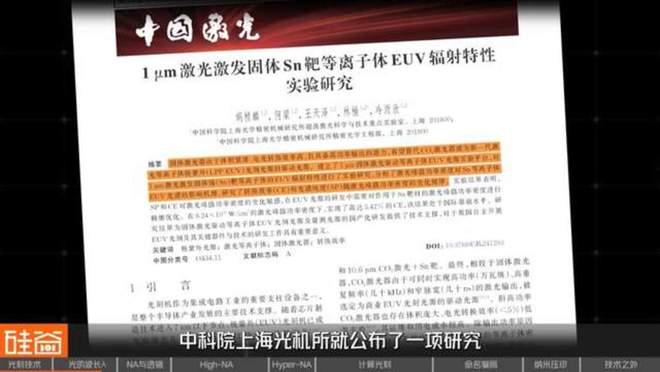
比如今年 3 月,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就公布了一项研究,称可以在 ASML 采用的 LPP 方案中,利用固体激光器替换原有的二氧化碳激光器,同时将液态的锡滴替换为固体锡,由此可以缩小光源结构并增大输出功率。
除了 LPP 外,还有 DPP、LDP、SRS、FEL 等方案,具体细节我们就不深入了。有消息称,华为东莞工厂正在测试基于 LDP 的 EUV 光刻系统,不过初期光源功率只有 80W,计划于 2025 年第三季度进行试生产。

总结一下,EUV 光源的演进非常具有挑战,预计还会持续多年的情况下,目前提升光刻机精度的手段,就要落在数值孔径 NA 上了。
03 数值孔径 NA
“对不起,你得把内裤也脱掉。”
如果你在蔡司的无尘室里听到这句话,可千万别当成一句玩笑,因为在进入前,不仅要穿上无尘服,而且内衣也必须换成无纤维的。
这些严格的清洁措施,是为了确保高数值孔径(High-NA)透镜生产时的无尘环境,因为精度要求太高了,容不得一点灰尘。

Cathy 光学工程师: 把一个 30 厘米尺寸(的透镜),如果你想象它放大到德国这么大,它的表面不平整度就只有一个足球这么大,这就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如何理解它的不平整性。
为什么 High-NA 透镜的精度要求如此高呢?在解析 High-NA 之前,我们先来解释下,数值孔径 NA、与 High-NA 是什么。
Chapter 3.1 NA 与透镜组:最接近“水滴”的人造物
在 DUV 光刻机的结构中,光线要通过一组硕大的透镜组,才会打到晶圆上,NA 表示这些透镜收集光线的能力。
假设这里有一块凸透镜,当一束光进入凸透镜时,光路会改变,所以凸透镜能聚焦光线,提高亮度或者光的能量。但如果光的射入角度过大,凸透镜将无法完成这个角度光线的折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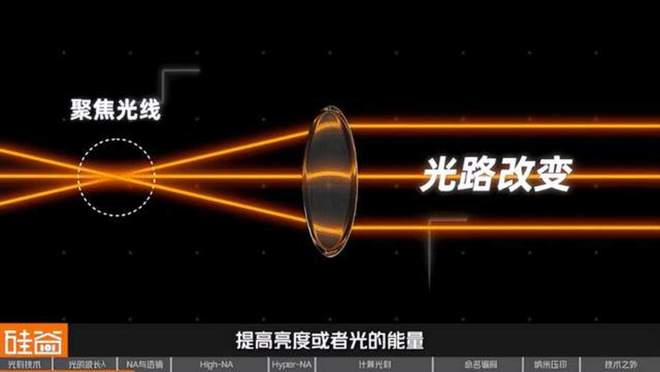
所以要提升 NA 值,要么在焦距不变的情况下,把凸透镜面积做得更大,要么增加凸透镜的曲率,也就是变得更厚。

你可能会疑惑,既然一个凸透镜就能完成光线的聚焦,为什么光刻机中需要那么多透镜呢?简单来说,因为球面镜存在像场弯曲的现象,导致成像打到晶圆上时会被扭曲。
另外还会存在各种像散、畸变、慧差等问题,所以需要加入各种透镜来补偿画面,将一片曲率大的透镜分成多个曲率更小的透镜,减小光学系统的误差,这就形成了硕大的透镜组。

相机镜头的原理也和光刻机类似,有句玩笑话说“摄像穷三代”,大家的钱主要献给了这些复杂的镜头设计了。
但到了 EUV 光刻机上,结构就不太一样了,由透镜变成了反射镜。主要原因就在于,EUV 光线会被其他介质吸收,这时不论是透镜还是水都用不上了。

Cathy 光学工程师: EUV 光刻机的透镜用的不是传统的透镜,而是反射镜,反射镜也不像是传统的大家熟悉的镜子去做金的镀膜,而是用一种叫做布拉格反射的技术。布拉格反射的原理其实就像一个衍射光栅,衍射光栅的原理跟蝴蝶的翅膀非常像,它是有很多微小的结构在上面。然后当光打上去的时候,如果光波的波长对的话,它就会从特定的角度反射出来,它的表面的光滑度要到一个纳米以下,就是一个原子尺寸的一个精度。

所以到了 EUV 光刻机上,要增加 NA 值,就得把这样一块光滑得像《三体》中“水滴”的反射镜做得更大。
Leo Pang(庞琳勇) 斯坦福博士、SPIE Fellow 美国 RevoLinx 公司总裁: 那你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再做得更大呢?实际上做到差不多两米,就差不多到极限了。它的(表面)平整度现在已经到一个原子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是已经没办法做大了。
有趣的是,在其他业内人士看来,相比其他部件,制造更高 NA 的透镜都不算难事儿,那 High-NA EUV 遇到的真正挑战是什么?为什么英特尔抢先订购了两台,而台积电却犹豫了很久?
Chapter 3.2 High-NA EUV:变形镜片
2014 年,ASML 参加了硅谷的一个技术展示会,展出了初代的 EUV 光刻机实验品。不幸的是,由于光源功率不足,展示过程非常失败,这样的结果一度让台积电对 EUV 光刻机的信心降至冰点,同时美国分析师也嘲讽道“摩尔定律已死”。

然而就在同一时间,第二代 EUV 光刻机,也就是 High-NA 的研发工作却已经开始了。为什么第一代 EUV 还没准备好时,High-NA 就开始研发了呢?
Cathy 光学工程师: 当他们设计(第一代)EUV 的时候,大家很显然地说是会排列一下,说哪些是技术难点。最开始肯定的是光学非常困难,因为光的波长也换了,极紫外光非常地不好控制,所以光学系统一定是最难的,然后可能是掩膜比较难做,然后可能是材料比较难做,然后最后就是光源。 但是事实上蔡司很早就把第一个事情来解决了,他们以为是很难的东西,并不是最难的东西。最后发现光源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案。

来源:zeiss
第一代 EUV 还在解决光源问题时,蔡司早早地就解决了透镜难题,转而去研发第二代 High-NA 了,那为什么 ASML 不一开始就用更大的 NA 呢?
Cathy 光学工程师: 举例来说,光刻机基本的概念是把它的掩膜,进行一个缩小倍数。他们之所以没有选择一个更大的(NA)参数去做,并不是说光学系统本身做不到,而是如果当它的(NA)倍数过大的时候,(掩膜图案)它缩小得过于小,会引起其他一些系统参数的下降。如果它的放大倍数过大的时候,或者说它的 NA 相差过大的时候,它的景深变得过小,那么当它芯片的上下有一点点波动,放置的位置有一点波动,或者光刻胶的厚度比较厚的时候,它会造成高一点和低一点的地方得到的效果不一样,这就会造成系统其他级别的误差。
同时 NA 和它的放大倍数有关,如果它的放大倍数过大的话,它每次只能刻一点点芯片,那么它刻完整个 Wafer(晶圆)的时候,它需要的时间就非常多。导致客户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这些芯片,每个芯片的成本也就更高。 EUV 还有一些其他的效果,比如说它的(反射)角度过大的时候, NA 过大的时候,光学的偏振效应会显现出来,这也需要再有后期的 correction(矫正)。但是当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补偿的时候,大家就会说那可能还是以前不是那么大的 NA 比较好一些。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High-NA 需要预计至少 500W 的光源,所以 ASML 一直在等待光源功率的提升。
简单总结下,提升 NA 后,会导致缩放的倍数更大,也就是打到晶圆上的图案更小,这就会降低光刻速度,同时也会引起其他参数的改变,反而需要花更多精力修正回来。
那么 High-NA EUV 是如何提升的 NA 呢?这就要说到“变形镜头”Anamorphic Optics。

变形镜头是水平与垂直方向具有不同放大率的透镜组合,比如在水平方向上压缩 8 倍,提高有效分辨率,在垂直方向只压缩 4 倍,来补偿景深损失,降低光刻胶不平整度带来的误差。
这样就相当于把一个正方形图案,压缩成了长方形,所以它被称为“变形”镜头。

Cathy 光学工程师: 在电影行业里面,其实现在是非常广地在使用 Anamorphic Optics(变形镜头)的原理。
ASML 官方宣称,High-NA 相比第一代的 Low-NA EUV,将光刻机的 CD 从 13nm 降低到了 8nm,打印的晶体管大小可以缩小 1.7 倍,让芯片制程推进到 2nm 的节点。

早在 2023 年 12 月,ASML 就向英特尔交付了全球第一台 High-NA EUV 光刻机,后来第二台也被英特尔收入囊中。
英特尔对 High-NA EUV 非常积极,但全球第一的芯片代工厂台积电却犹豫了。其中最大的原因呢,还是在于“钱”。
由于 High-NA EUV 光刻机的设计更复杂,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第一代 Low-NA EUV 价格为 2 亿欧元,但到了 High-NA 上,价格来到了 3.5 亿欧元,也就是涨价了 75%。

Leo Pang(庞琳勇) 斯坦福博士、SPIE Fellow 美国 RevoLinx 公司总裁: 它一下子比以前贵了很多,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光刻)效率反而是变低了。 虽然它(ASML)说它的(晶圆工台)移动的速度是变快了,但也没有变快两倍。所以最后就变成,你还要去考虑这两个 Mask(掩膜板)怎么把它最后的芯片,能够接的时候接得不错,而且这两个 Mask(掩膜板)还要相互换,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Intel 就说那我们要把这 Mask(掩膜版)做成一个(长方形),不是原来那个方的了,让它可以一次印出来。但是至少目前整个行业对此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所以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台积电就觉得(High-NA)这个东西花费太多,它的收益没那么好。它如果不用 High-NA 的话,它就去做(Low-NA)EUV 的 Double Patterning(双重曝光),或是 Triple Patterning(三重曝光),分辨率的提高实际上更大。所以就是各自有各自的考量。
由于 High-NA EUV 采用了变形镜头后,反而使光刻的效率下降了,再加上目前行业对于如何使用 High-NA 还没有达成共识,而且第一代的 Low-NA EUV 也能通过多重曝光,来生产 2nm 芯片,因此台积电对是否订购 High-NA 非常犹豫。

不过犹豫归犹豫,High-NA EUV 依然是下一代光刻不可或缺的设备。所以我们看到,台积电在 2024 年下半年依然决定下单了。
可既然英特尔早在 1 年半前就拿到了 High-NA EUV,为什么如今还没能正式量产 2nm 以下的芯片呢?
Leo Pang(庞琳勇) 斯坦福博士、SPIE Fellow 美国 RevoLinx 公司总裁: Intel 它这次的话确实比较激进,所以它在这个机器还没有完全 ready 的时候,它就把这个机器拿进来了,因为 High-NA 的机器它现在不是说在 ASML 的工厂里边装好了,然后拆了再过来,现在是每一个它的 component(零部件),都是直接从它(ASML)原来的供应商那就直接到了 Intel,然后在这第一次把它组装。所以从它的调试的进度来看的话,它其实还是挺快的。

今年的 5 月中旬,英特尔宣布其 18A 制程,也就是 1.8nm,进入了风险试产阶段,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后续进展。
Chapter 3.3 Hyper-NA EUV:芯片行业的回光返照
虽然 High-NA 还没能正式用于量产芯片,但 ASML 已经在 2024 年 6 月,提出了下一代的 EUV 光刻机,那就是 NA 值提升到 0.75 的 Hyper-NA EUV,预计将于 2030 年面世。

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一样,提升了 NA 值后,会导致光刻机的焦点过小,这也对系统的其他部件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比如与 ASML 合作开发光刻机的 Imec 先进图案化项目总监 Kurt Ronse 表示,在 High-NA 时,就已经将晶圆上的光刻胶涂抹的更薄了,到 Hyper-NA 时,如何涂抹光刻胶也将会是更大的挑战。

在嘉宾看来,Hyper-NA 距离实际应用还太遥远,接下来十年内,光刻机的重点依然是 High-NA。
Cathy 光学工程师: 每一代的 NA,因为它是和其他系统参数平衡的结果,所以每一代的 NA 都是至少是持续十年的。我们可以认为现在这样一个 0.55 的(High)NA 应该是接下来几年主要统治的方向。
不过对于 Hyper-NA 真正的挑战并不是技术难题,而是商业难题。

Marc Hijink 《新鹿特丹商报》(NRC Handelsblad)记者著有《芯片制造——光刻巨头 ASML 传奇之路》: 一如既往地,这些设备可能非常昂贵。而对相关行业而言,关键在于它们只能购买能真正创造附加值的设备。因此这些设备必须具备经济可行性,而这正是 ASML 当前研究的课题。
根据预测,Hyper-NA EUV 的造价可能会达到 6 亿多美元,但相比 High-NA 能将 CD 降低到 8nm,Hyper-NA 仅能降低到 6nm,台积电连 3.8 亿美元的 High-NA 都嫌贵,那 Hyper-NA 是否还会有市场?或者说是否有必要呢?

Leo Pang(庞琳勇) 斯坦福博士、SPIE Fellow 美国 RevoLinx 公司总裁: 我觉得还会有市场。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几年前的时候,半导体(行业)大家还是挺疑虑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认为平板电脑或者是笔记本电脑,已经跑得足够快了,没必要再往下做了,但是 AI 就出来了。 当你有了大模型之后,GPU 的算力什么之类的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它能够把它(GPU)卖 3 万美金、4 万美金,而且还是供不应求,这就说明它(芯片)能够产生的价值,是远远大于它的成本。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大模型出来之后的话,半导体确实又从我们以前的很多年都觉得是个夕阳产业,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朝阳的产业了,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简单总结下,目前最尖端的 High-NA EUV 预计今年下半年用于芯片量产,并将主导光刻机行业十年左右。虽然下一代 Hyper-NA 的成本暴涨,但随着 AI 的发展,芯片行业似乎又回到了朝阳产业。而 AI 不仅带动了芯片的需求,甚至还推动了光刻机的进步。
04 工艺因子 K1 与计算光刻 Chapter 4.1 精密制造:“屁大点事”带来的生产灾难
过去,在英特尔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工厂内,每到夜深人静时,光刻机的产量总会莫名其妙下降几小时,这段时间内,工厂几乎无人操作,唯一的改变,就是工厂外会刮起一阵风。
听上去是不是非常玄学?研究人员经过长时间排查,最后发现原因竟然是“屁大点事”。
原来这个工厂附近有一家奶牛场,每到凌晨 1 点时,风向会发生改变,将奶牛们放的屁吹到工厂里,由于屁中含有甲烷,会通过空气净化器进入无尘室,最后导致了芯片生产时良率降低。

Marc Hijink 《新鹿特丹商报》(NRC Handelsblad)记者著有《芯片制造——光刻巨头 ASML 传奇之路》: 所以英特尔只有一次机会,他们不得不收购周边的奶牛场,以排除潜在问题。因此,必须借助软件来预测那些微小的偏差,并确保机器的稳定运行。 毕竟对 ASML 来说,预判设备日常运行状态至关重要,因为半导体制造系统的脆弱程度远超常人想象。
任何一点参数的改变,都会影响光刻机的生产。所以近年来,ASML 也开始利用 AI 来提升光刻机的生产精度。
对芯片制程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就是工艺因子 K1,代表的是掩模、光源、光阻等各环节的成像性能和工艺复杂度。K1 越小,表示工艺提升越多、CD 越小。

而目前 K1 最大的提升点,就在于光瞳与掩膜板,由此诞生了“计算光刻”(computational lithography)。
Chapter 4.2 计算光刻:用假图案刻出真芯片?
我们先来了解下,为什么会需要计算光刻。在光刻机中,光线会将掩膜版上的电路图给打到晶圆上,但如果直接将最终的电路刻在掩膜版上,成像的画面可能会模糊不清。

这个原因其实大家在高中物理课上就学过。如果让光穿过一个非常狭窄的缝,它就会触发“波”的特性,向四周“散开”,进入原本照不到的地方,这就叫做衍射。
而如果有两条缝,相邻缝隙之间通过的光会叠加,产生干涉现象,最终显现出来的是多个或明或暗的条纹。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光的双缝干涉实验,所以为了能提升光刻精度,才有我们前面说的,尽量减小光的波长,降低衍射效应。
但当光的波长固定时,大家该怎么做呢?这就得利用计算光刻了。
计算光刻主要从四个方面下手:光瞳形状、光源、掩膜版、波前优化工具。我们先来看光瞳。

光瞳上会有不同的图案,将光线调整成一定的形状,从而减轻某种方向上的干扰。比如我们要打出全是竖条的形状,就采用这样形状的光瞳,降低横向光照的干扰。

掩膜版电路千变万化,但光瞳的形状比较固定,所以 ASML 对光源模块做出了一些优化,设置了非常多微小反射镜组成的阵列,名为 Flex-Ray,用来控制局部光照,从而提高成像的分辨率。

同时,由于光的衍射与干涉,会让最终成像变得扭曲。
此时可以在掩膜版图案上的边角处增加一些额外的小孔,增强局部的进光量,就能修正最终成像了。这个过程被称为光学临近效应修正(O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简称 OPC。

但光本身也带有能量,当光通过透镜时,会加热镜片,镜片由于热胀冷缩,成像产生畸变,此时就需要波前优化工具来计算、并加热透镜组中共轭镜的对应位置,修正图形。

值得一提的是,计算光刻并不仅仅是修正光学误差,还有其他的物理、化学因素造成的不完美。
Chapter 4.3 逆向光刻 ILT:AI 对产业的影响
随着芯片的电路图越来越复杂,OPC 也经过一轮进化,来到了逆向光刻技术(Inverse Lithography Technology),ILT,这也是目前提升 K1 的最重要的方式。
我们的嘉宾庞博士正是因为对 ILT 的贡献,在 2023 年时当选了 SPIE Fellow,这是光刻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Leo Pang(庞琳勇) 斯坦福博士、SPIE Fellow 美国 RevoLinx 公司总裁: (ILT)我在 Mask(掩膜版)上的 Pattern(图案)可能跟你要印的东西是长得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要印这么一个洞,那我反算出来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洞,它是可能中间有一个洞,然后旁边有很多的环。那这个的话 OPC 就做不出来了,因为 OPC 你不知道它会长成那个形状。所以 ILT 的话,你可以把它认为是全局的一个优化,把它算出来的。

OPC 是“正向”调整掩模图案,比如添加辅助图形、修正边角,这种方法更依赖人工规则,适用于相对简单的图形,计算量较低。而 ILT 则是利用 AI 算法,“逆向”求解出最优掩模图案。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OPC 就像一家公司啥都自己做,想要达成什么效果,还得衡量下自己有没有足够实力做出方案。而 ILT 就像去找外包公司,你作为甲方,只要告诉乙方:我就要这个结果,甭管你用什么方式,做出来就行。
随着 ILT 的出现,芯片的设计与光刻也迎来了一轮改进。比如庞博士最为人熟知的贡献,就是将曲线逆向光刻技术引入了光刻和光掩膜领域:之前芯片里的布线必须要横平竖直,否则无法制造对应的掩膜版。
但有了 ILT 就可以做出曲线的掩模。这样一来,芯片布线可以变得更灵活、更紧凑,晶体管的堆叠、更小、更密。由此带来的芯片提升,甚至比 NA 的提升还要大。
Leo Pang(庞琳勇) 斯坦福博士、SPIE Fellow 美国 RevoLinx 公司总裁: Imec 最近他们讲的就是,我们的芯片上这 Pattern(图案)如果变成 Curve(曲线)的话,他可以提升三代。所以这比从 EUV 的 High-NA 到 Hyper-NA,对这个行业的贡献还要大。

来源:Imec
如何提升 ILT 呢?回到我们刚才的比喻,如果你想提升外包公司干活的效率,简单!多给钱就行。而在 ILT 中干活的是 AI 算法,提升算力就能变得更强。
Leo Pang(庞琳勇) 斯坦福博士、SPIE Fellow 美国 RevoLinx 公司总裁: 那当然(ILT)它算的这些方法的话也跟那个(OPC)不一样,就是 OPC 它基本上是在这个 Polygon(多边形)上面去做的,然后 ILT 的话,它全部是在这个 Pixel(像素)上,像我们做的后来的话,也都是用 GPU 来做这个加速,因为 GPU 它是最适合做这个 Pixel 的这种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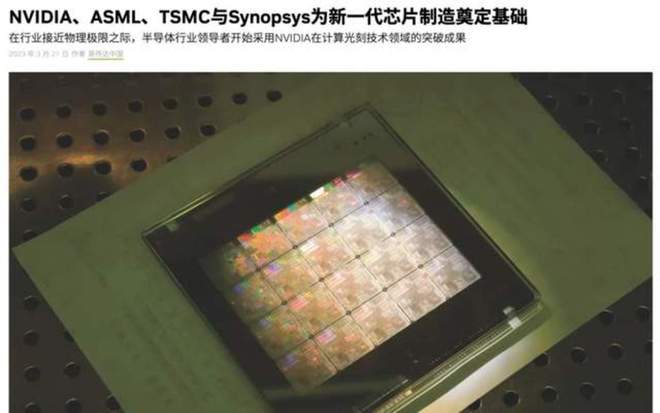
来源:NVIDIA
Marc Hijink 《新鹿特丹商报》(NRC Handelsblad)记者著有《芯片制造——光刻巨头 ASML 传奇之路》 因此,它们(ASML)正在从 CPU 转向 GPU。为此,它们采用了目前由英伟达提供的最先进的 GPU。并且它们将计量技术视为提升光刻能力的一部分,甚至在遥远的未来也是如此。
当然,除了计算光刻外,其他流程也会提升光刻机的制造精度。比如芯片制造完成后,会使用 ASML 的电子束量测工具检查缺陷,并将检测数据计算后,反馈至光刻机台,修正后续的生产数据。

更强的芯片能提升光刻精度,更高的光刻精度又能生产更强的芯片,有点“左脚踩右脚上天”的意思了。
05 光刻技术还能走多远?
光刻技术还能走多远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说到,光刻机的精度其实还与很多零部件相关。

比如掩膜版,它的移动加速度可以达到 32g,大约是过山车的 8 倍。
再比如晶圆台,得处于“浮空”的状态,为的就是将移动的精准度控制在纳米级别。
Evan Tao TetherIA 联合创始人兼 CEO ASML 前机械设计工程师: 这个台座它是采取磁悬浮的状态,一个物体在空间有六个自由度,因为当时我说的有 Twin Station(双工作站),就是 Twin Scanner(双扫描仪),根据那边扫描过的表面平整,它把这个数据记录下来,(后续)在曝光的时候,它根据那个平整的误差,它要及时进行(高低)调整,这样才能保证去修正它的不平整性。

还有晶圆台的表面平整度,高度误差要低于 10nm,为此 ASML 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
Evan Tao TetherIA 联合创始人兼 CEO ASML 前机械设计工程师: 从 ASML 角度来说,它有一些模组,应该是对平整度要求极高,所以它需要专门成立这么一个部门,去解决一个 Traditionally(传统的)、听上去非常简单,或者是比较普通的一个工作。
还有很多因素就不一一举例了,正是因为芯片生产有太多干扰,所以我们定义是否攻克某个制程时,往往以“良率”是否足够高为标准,而不是生产出样片就完事了。

接下来总结下光刻机三大核心的现状:
1. EUV 光源还在攻克更高功率,极紫外光会使用到 2035 年甚至 2040 年。
2. High-NA 即将投产,预计在 10 年内都是主流。
3. 芯片性能与 AI 算法的进步,将进一步带动光刻机的提升。同时短期内,光刻机的提升也会更依赖 AI 算法。
到这里我们也来尝试回答最开头的问题:芯片性能是否已经达到了物理极限?科技会就此锁死吗?
Chapter 5.1 3nm 的真相:营销与竞争催生的“文字游戏”
我们在之前《傲慢、短视、扼杀创新,垄断巨头英特尔是如何走向倒塌的?》的文章中有提到,他们推出“Intel 7”工艺时,实际是 10nm 工艺的改良版,但当时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删掉了一段内容:
玩这种文字游戏其实不怪英特尔,因为台积电与三星的工艺也不太厚道。虽然英特尔采用 10nm 工艺,但晶体管的实际密度已经高于了台积电和三星的 7nm,所以为了不在宣传上落下风,才改名为了 Intel 7。

其实我们一直被“骗”了,厂商们宣传的什么“5nm”、“3nm”,实际尺寸甚至都没有低于 20nm。
那么芯片工艺命名中到底掺杂了什么鬼?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简单科普下芯片结构的演进。
在 28nm 之前,芯片上的晶体管都是这样的平面结构,那时命名的方式,以晶体管的栅极长度(Gate Length)为准,这样大家就能大致判断晶体管有多大、密度有多高,这也对应着芯片的性能。

但随着晶体管越做越小,由于量子隧穿效应,晶体管就容易漏电,具体的原理我们就不多解释了,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工程师们决定让晶体管长出“鱼鳍”,变成了名为 FinFET 的立体结构。

结构大变后,要判断晶体管的大小,就不能只看栅极长度了,毕竟有的结构可能一个栅极对应了很多个“鳍”,这时就得综合考虑鳍片宽度、鳍片间距、栅极间距等等参数,才能判断晶体管的大小或密度。

既然没有一个标准可以衡量芯片性能,那肯定数字越小越好对吧,此后芯片的工艺命名,就是厂商们自己说了算了。
像我们开头说的日本 Rapidus 公司,通过和 IBM 合作,在 7 月 18 日宣称自己试产了 2nm 芯片,但根据 TechInsights 的报告,这款芯片只能算 3nm。

Leo Pang(庞琳勇) 斯坦福博士、SPIE Fellow 美国 RevoLinx 公司总裁: 当然这个风气的话,最早是台积电搞起来的,那个时候台积电还落后于 Intel,所以它整天到晚想着,说怎么跟 Intel 去竞争呢?那他就开始把他每次往下的时候,他就不是讲他真正的线宽了,他就说每次我就是乘以 0.7,所以我这个什么 28nm,完了就是 20nm,然后就是 16nm,然后完了就是 12,然后就是7,所以它到最后的话,就是这个几纳米,跟上面的线宽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现在 2nm 的话,它上面的线宽实际上也是二十几纳米,或者说(Fin)Pitch(鳍片间距)是 30 多纳米,这是他能够做到的极限了。
所以芯片上的晶体管,不论是尺寸还是间距,都还远没有达到命名上的几纳米,现在的命名逻辑,主要参考的是晶体管密度,这也意味着,芯片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近年来厂商们更是转向了 GAAFET,相当于从平面结构的平房,升级到 FinFET 的两层房,再升级到 GAAFET 的多层房,虽然这些房子的占地面积相同,但流过的电子数更多,就相当于房子住的人更多了,也变相提升了芯片性能。
Marc Hijink 《新鹿特丹商报》(NRC Handelsblad)记者著有《芯片制造——光刻巨头 ASML 传奇之路》: 但如果你看看这些结构的真实尺寸,这些线宽通常有 20 至 30 纳米。所以很多说法其实更多是营销炒作。 据 ASML 透露,至少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在原子级的问题真正成为瓶颈、系统变得不可预测之前,技术发展至少可持续至 2040 年后。事实上,现在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或者说,其实还有很大的“缩小”空间。
回答开头的问题,由于现在芯片上的尺寸还远没有达到几纳米,所以还有很多提升空间。而 ASML 官方认为,至少在 2040 年之前,我们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Chapter 5.2 纳米印压:“活字印刷”生产芯片
如果把传统的光刻机比作一台激光打印机,纳米压印光刻术(简称 NIL)就是活字印刷术。
它的核心原理就像“盖章”一样,把电路图案“压”到晶圆表面,在光刻胶上形成图案,通过紫外光固化光刻胶,后续再进行显影、刻蚀等步骤。

主流有三种方法,分别是:热压印、紫外压印、微接触压印,具体原理我们就不多赘述了。
这项技术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 1995 年,华裔科学家周郁(Stephen Chou)就首次提出了纳米压印概念;2003 年,NIL 被纳入国际半导体技术蓝图(ITRS);直到 2004 年,日本光刻机制造厂佳能开始深入研发。

Leo Pang(庞琳勇) 斯坦福博士、SPIE Fellow 美国 RevoLinx 公司总裁: Nano-imprint(纳米压印)的话就是在 EUV 出不来的时候,大家想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当然日本的印刷一直是做得挺不错的,其实他们还是蛮有底蕴的。所以像 Canon,他后来因为就是觉得说,已经是没有办法跟 ASML 再去竞争了,所以 Canon 就开始去跟 DNP(Dai Nippon Printing 大日本印刷),然后他们就去合作,就说我们来做(纳米)压印。
2023 年 10 月,佳能推出了第一代可量产的纳米压印光刻设备,号称实现了最小线宽 14nm,相当于 5nm 制程。
同时佳能宣称,未来有望实现最小线宽 10nm,相当于 2nm 制程。

Marc Hijink 《新鹿特丹商报》(NRC Handelsblad)记者著有《芯片制造——光刻巨头 ASML 传奇之路》: 但它尚未像光刻那样在大规模应用中得到验证,而且在实现大规模量产方面还面临一些挑战。
目前纳米压印遇到的挑战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模板成本高。传统光刻的掩膜板比实际电路大了 4 倍,制造成本相对较低,而纳米压印需要1:1 的模板,制造难度极大。同时,由于模板会与光刻胶和晶圆直接接触,会因磨损导致精度下降,需要频繁更换,这也带来了更高的生产成本。

第二是产能较低。ASML 最新的 High-NA EUV 每小时可生产 185 片,就这都被台积电诟病,而纳米压印每小时的产量只有 100 片,平摊到每个芯片上的成本就更高了。
第三是良率低下。由于纳米级电路非常脆弱,模板脱模时非常容易断裂或变形。同时,我们前面提到现在芯片变成了“多层”结构,压印电路时需要将不同的模板一层层对齐,这其中的误差控制难度也高于投影式光刻。
另外,光刻胶的涂抹的平整度要求也更高了。

综合以上缺点,纳米压印在尖端芯片领域推广起来还是有一些困难,但用在结构简单、缺陷容忍度高的存储芯片领域却很合适。
Leo Pang(庞琳勇) 斯坦福博士、SPIE Fellow 美国 RevoLinx 公司总裁: 所以他后来主要的想法是,能够用在像 Nand-Flash(NAND 闪存)上面,因为是存储,所以它有些地方不工作,其实没什么关系。 但最近他们其实发现了,因为现在 Packaging(芯片封装)变得很火了,它的好处是因为那个东西很大,所以它其实不是说局限在一个 Wafer(晶圆),一个小的 Chip(芯片)上。所以现在有些想法是说,用这个技术能够去做这个 Packaging(芯片封装)的部分,这可能我觉得它是它的一个优势。
06 ASML 的挑战:不只技术问题
如今美国希望将芯片产业回流,包括推出了《芯片法案》,要求台积电在美国建厂等。虽然外界一直不看好在美国生产芯片,但说到 ASML 加大在美国的生产时,我们的嘉宾却认为这是完全可行的。

Evan Tao TetherIA 联合创始人兼 CEO ASML 前机械设计工程师: 因为它这个行业毕竟和消费电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对人工成本的敏感性会低很多。我当时在的那个 site(地点),实际上就是美国最大的生产 site(地点)。当时我离开的时候大概有 2000 多个人,现在估计有翻一倍, 4000 多人差不多很有可能,那个地方也是一直在扩建。 所以如果说他是想要更多的在美国制造,我觉得是完全可行的。

然而,随着美国发起关税战,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 ASML 将生产线搬迁至美国的决心,给 ASML 股价带来了不小压力。ASML 作为一家荷兰公司,为什么会受到美国政策的限制呢?
一方面,ASML 光刻机中的许多核心零部件,都用到了美国公司的技术。比如极紫外激光器,来自于 ASML 收购的美国公司 Cymer,所以不得不受到美国商务部的管制。
另一方面就比较有意思了,那就是 ASML 的崛起,有部分原因是来自于美国政府的扶持。
1999 年,美国发起了“EUV-LLC”项目,用于推动 EUV 的技术研发,这个项目是为了巩固美国在芯片行业的先进地位,但 ASML 却和美国能源部达成了协议,参与到了其中。

此外,ASML 还有许多关键技术,来源于 2001 年收购的美国公司 SVG(硅谷集团)。要知道,SVG 的许多业务涉及到军工,然而最终美国政府依然批准了这项收购,只要求剥离 SVG 下属的 Tinsley 部门(军用光学产品部门)。
之所以美国愿意扶持 ASML 这个“近邻”,其实是为了打压“远亲”的日本半导体产业,具体细节因为篇幅原因我们就不细说了。
正是因为 ASML 与美国之间有多项交织,所以受制于美国政策。而 ASML 拥有 5000 多家供应商,供应链复杂度不比苹果低,它们的生产是否会受到影响呢?
Evan Tao TetherIA 联合创始人兼 CEO ASML 前机械设计工程师: 我在阿斯麦和苹果都工作过。从产品质量的角度来看,阿斯麦你可以想象,每一个零件都是手工雕琢出来,他可以承受这样的高精度的需求,他可能生产 100 个零件有 99 个都报废的,那留着你一个是达到他要求的,甚至说它每个零件的尺寸有误差,最后(通过)弥补出来成为我需要的那个值,它可以用这样方式来实现它目的。 但是苹果是不一样的,你是规模性生产,你要考虑的是就是统计学上的这些问题,正态分布,简单来说就是说你怎么能够保证你的产品几万、几千万都是 consistent(一致的)?

所以目前看来,光刻机生产不会受到影响。
但 ASML 的 CEO Christophe Fouquet 也在今年 7 月中旬警告称,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ASML 可能无法在 2026 年实现增长,由此也引发了最近股价的大幅下跌。
有意思的是,Christophe 也因此被股民一顿狠骂,大伙觉得你咋就那么实诚呢,本来财报不错非要降低未来的展望指引,把股价打成这样。

这让我也想到在去年年底时,ASML 也因财报提前泄露,导致了股价大幅下跌。
而在传记作者 Marc 看来,这就是 ASML 企业文化很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它生产着全世界最精密的仪器,但另外一方面在企业管理上又经常出现疏忽。
Marc Hijink 《新鹿特丹商报》(NRC Handelsblad)记者著有《芯片制造——光刻巨头 ASML 传奇之路》: 这件事其实有点好笑,因为当财报提前泄露发生时,我正好和 ASML 的一些人坐在一起。他们当时相当慌张,因为是软件或技术故障出了问题,导致某份本不该公开的文件被发布到了可以被追踪的网页服务器上。这是一个本可以避免的错误,但却很典型地体现了 ASML 的风格。 这正是 ASML 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总是在赶进度,总是被各种截止日期催促。在这种节奏下,人们往往容易忽略那些看起来没那么重要的问题。
虽然各国在光刻产业上存在政治与利益的分歧,但我们从大众的角度看,依然希望能看到这项技术的进步。因为光刻机投射的,远不止晶圆上的纳米电路。
AI 大模型的狂飙突进、深空探测器的遥远征途、深海奥秘的精准测绘、基因图谱的快速解析无不依赖于这台精密机器。
或许石刻是文明最后的墓碑,而光刻却是文明前进的引擎。






